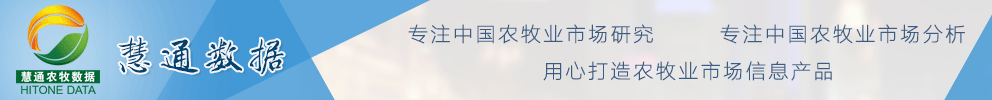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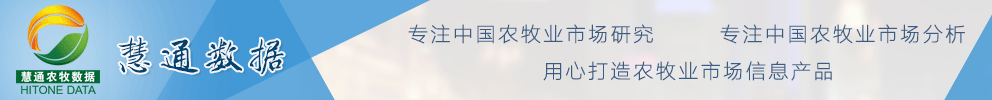
慧通综合报道: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价格调节基金,这个已经存在了24年的基金,不仅其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而且,更有多地价格调节基金,曾被财政部以“乱收费”的名义叫停。
在陈洪德看来,可以“设立”和可以“征收”完全是两个概念,赋予地方政府设立价格调节基金用来调控价格,并没有授权政府可以向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征收价格调节基金
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听说过价格调节基金,但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价格调节基金的确与每个人的钱包密切相关。
在广东,每升汽油中包含2毛钱的价格调节基金;在海口,买一辆10万元的车,需缴纳价格调节基金300元:在河北,外来建筑单位要按注册人数每人每月征收2元的价格调节基金。
安徽省黄山市更是规定,在黄山市的中央、省属企事业单位,按职工月工资总额的1%征收价格调节基金。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价格调节基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已经存在了24年的基金,不仅其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而且,更有多地价格调节基金,曾被财政部以“乱收费”的名义叫停,甚至目前,财政部门内部仍然将其定性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越权成立的政府基金”。
但是,这个基金却表现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尤其是去年以来的通胀高企,更是加速了地方重启价格调节基金的热情。
而据记者调查,也是因为该基金模糊的法律边界,更导致全国各地存在着诸多价格调节基金的收取乱象。有专家认为,随意征收价格调节基金,实际上加重了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负担,应当规范该基金的征收。
价格调节基金乱象
所谓价格调节基金,是指专项用于政府平抑物价、平衡供求、稳定市场,重点用于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的基金。同时,它也对因居民重要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基本生活受到影响的低收入群体给予适当补贴。但实际上,在全国各地,这种基金却以一种混乱的面目示人。
到过三亚的游客,如果留心门票上的字样,你就会发现,实际上,你在三亚旅游的每一天,都在往当地的价格调节基金里投钱。
著名景区蜈支洲岛门票168元,其中8元为价格调节基金;普通景点蝴蝶谷门票33元,其中含有3元政府价格调节基金;在三亚住宿也需要交纳每晚2元到11元不等的价格调节基金。
随着国际旅游岛效应的逐步显现,三亚2011年接待过夜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从数元到十数元价格不等的调节基金也就意味着,这些游客为三亚当地贡献了一笔不菲收入。
三亚市物价局新闻发言人陈金波对本报记者表示,游客能贡献的价格调节基金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资金来自于房地产交易。
[ 陈洪德认为,价格调节基金的目的在于调控市场、稳定市场,但地方政府这种随意征收的行为实际上却是加重了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负担]
按照三亚价格调节基金的相关规定,外埠企业投资三亚房地产需要缴纳相当于工程造价3%的价格调节基金,商品房进行交易时也需要缴纳销售额的千分之三作为价格调节基金,由交易双方平均分摊。
在陈金波看来,三亚市价格调节基金的管理非常严格,与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由地税部门代征不同,三亚市物价局下设三亚市价格调节基金征管办公室负责全市的征管工作,征收之后交由财政专户管理,物价部门只能为这笔钱的使用提出建议,使用发放均由财政部门负责。
而在离三亚不远的海口,购车和出海也被纳入了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范围。
2011年9月28日,律师陈洪德在海口购买一辆22.69万元的轿车时被海口市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委员会征收了776元的价格调节基金,若开着小车从海口港口过海去其他省,每车每次也要征收2元的价格调节基金。
陈洪德开始怀疑这些收费是不是政府乱收费。他用半年的时间对各地的价格调节基金的文件做了收集、整理和研究,他发现全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价格调节基金,而且,各地征收对象、征收范围以及征收比例更是五花八门。
追溯价格调节基金的前身,它起源于1988年国务院下通知建立的副产品价格基金,当时处于价格闯关时期,国务院要求大中城市建立平抑副食品的价格基金,基金来源可根据当地情况,多渠道筹集,具体办法由当地人民政府规定。
这个通知成为地方政府设立价格调节基金的最早依据,通知中所规定的“根据当地情况”以及“多渠道筹集”成为今天价格调节基金各种征收方式和乱象的政策根源。
据本报记者了解,国内各地市价格调节基金筹集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各级政府通过筹措财政性资金安排,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如北京市、江苏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珠海市等地;二是向社会征收,如广东省、长沙市、海口市等地;三是多方面筹集,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安排一部分,向社会征收一部分及其他来源,如湖北省、福州市、南宁市等地。
在征收范围上也是各不相同。有些地方规定,缴纳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纳税人,应当分别按照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1%同时缴纳价格调节基金,比如甘肃省和湖北省;成都市则按照纳税人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1%征收;贵阳市则为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当前价格调节基金的现状,那就是乱。”陈洪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对于价格调节基金的管理经费也有着不同规定,比如广东省政府的文件授权地方制定管理经费的标准,阳江市甚至规定了要提留高达10%的经费。
根据《阳江市价格调节基金征集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从征收价格调节基金中提取10%作为基金管理和征集的费用,其中代征价格调节基金的部门留5%,价格调节基金主管部门从价格调节基金中提留5%。
陈洪德称,高达10%的管理费用至少表明,价格调节基金已经成为地方有关部门的小金库,这也违背设立该基金的初衷。
被误读的《价格法》第27条
各地开征价格调节基金的依据主要是三个文件,除了上文中提到的1988年国务院通知之外,还有1993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1993〕60号),其中提到“已经建立了主要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的地区,要充分发挥基金的作用;尚未建立基金的地区要尽快建立起来”。
另外一个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就是现行《价格法》。《价格法》第27条规定,政府可以设立价格调节基金,调控价格稳定和稳定市场。
2009年,广西物价局向国家发改委发出《关于县级人民政府是否有权决定征收价格调节基金的请示》,发改委根据《价格法》第27条复函称:“县级人民政府有权设立价格调节基金。”复函并没有明确表示,县级政府是否能够征收,但有些地方也把这个文件看作是开征价格调节基金的依据之一。
在陈洪德看来,可以“设立”和可以“征收”完全是两个概念,《价格法》第27条规定仅赋予地方政府设立价格调节基金用来调控价格,并没有授权政府可以向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征收价格调节基金。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同上述这一看法。他认为,开征价格调节基金本质上和税收一样,属于对企业和公民财产权的分割,应该对法律采取从严解释。《价格法》既然没有明确征收,那就不应该解释为可以征收的方式来获取基金。
施正文表示,《价格法》只是提出政府设立价格调节基金,法律意义上的政府是五级政府,法律显然不可能授权五级政府全部可以征收价格调节基金,因此,可以明确这条是指在财政支出制度中设立价格调节基金,政府应该从财政资金中安排专门资金来设立这一基金,比如北京今年拿出5个亿来建立价格调节基金就是一种符合《价格法》原意的做法。
陈洪德认为,地方政府的做法,显然是故意曲解《价格法》的规定,以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及职责范围。